
农村里,腌瓜菜是夏日里浓墨重彩的最后一场戏了。
家家户户都会把瓜从地里扯上来,瓜藤全部清理掉。成堆的瓜放在大场上,男人女人围成一圈,小孩子如快乐的小狗,人群里钻进钻出。瓜被男人用刀,一剖两。女人则用汤勺细心地刮去中间的瓤。这刮瓤是很有讲究的,得把有瓜籽的角角壁壁都掏空,丝毫心慈手软不得,否则日后便成瓜菜腐烂的根源。烂了瓜菜,一秋一冬的咸便没有着落,这个玩笑是开不得的。所以,这等细心的活,非女人不可。家家的男人摆着手:这活儿玩笑不得,得娘子才能干的。女人脸上便都泛着好看的满足的红光,手里的汤勺刮得更欢了,即刻,面前便堆起了瓜的小山。
女人会起身,拿着那种特别的大的竹篮,把瓜拾进去。抱出家里早已编好的芦苇帘子,两端搁长条凳,长条凳上再横放两根长木棍,帘子铺排在上面,剖好净瓤的反便被仰躺在上面,白嫩嫩的身子隐约可见青青的皮。很长的帘子,排列整齐的瓜,很壮观的景象了。男人乐呵呵地收拾东西重新下地做活去了。女人等会也要去的,剩下的活便是孩子们的了。孩子们正是暑假,玩得狂野了,大人借此收住他们的心,对着瓜菜叮嘱:有雨要记得收回家,淋湿了烂掉仔细你的皮!孩子一路蹦跳一路逃走,忙不迭地答应着大人。站在中心的路上跳房子跳皮筋,眼睛却不时地斜睨着大场上晾晒着的瓜菜。真有闷雷一声,吓得皮筋也来不及收的,慌慌张张地把瓜菜收进大竹篮里,颠跛着拿进屋里,太阳又出来了。沮丧着再次拎出来。六月的神鬼天,如是几番,孩子们玩也不尽兴,索性坐在自家场上,遥遥相对着。却也闲不住的,干什么呢?唱歌。没几人唱得出真正的歌,一首《我爱北京天安门》颠来倒去地唱个稀巴烂。大人回来时,乐得脸成一朵花,长大似乎便是从看守瓜菜开始的。
瓜菜晒了正面,晒反面。青青的皮变得微黄时,便可以打卤腌制了。打卤也是个马虎不得的活。太淡了,瓜菜腌不住容易坏。太咸了,没法吃的。村里常打卤的老婆婆,东家打好西家请。被请的老婆婆,一律开心地答应着,并不嫌人们浪费了她的时间。外婆便常被人家请去,颠着一双小脚,忙碌却很开心。
在卤水里泡过一夜的瓜菜明显蔫了下去,还得捞起来再次晾晒。傍晚时,要把头一天的卤汁煮沸再用。村里便飘满瓜卤的咸香,转着圈儿往鼻子里钻。瓜菜越晒越瘦,瓜卤越熬越少,如此反复,几趟下来,瓜菜变成纯白的了,便大功告成了。装上一个大大瓦罐,压上一块重重的石头。这块石头作用可大呢,压得越实越不容易坏。吃的时候,搬掉大石头,取出一两条,水里洗净,切成片或丝,放在碗里,早晚就粥的菜便有了。讲究一点的,会拌上香油。由海门迁来的人,吃法更不同了,常会和着鸡蛋,或是黄豆米子炒一炒,这在我们这些本地人眼里,是大奢侈了。
后来在饭店吃过一道菜,油炸凤尾鱼一边伴着的又白又亮的丁状小物,吃在嘴里香香脆脆,却不识是什么东西,悄声问,却原来是腌制的瓜菜。是乡里的姑娘,突然穿上了城里的吊带裙,脸上还涂了胭脂花粉了,让我如何一眼就能认出它来?有关瓜菜的往事却款款而来。
村东头的小两口,腌制瓜菜远近闻名,老人们还在循规蹈矩地腌着白瓜菜时,他们早已尝试着放入酱油糖醋,腌出又咸又甜的五味俱全的瓜菜来了。他们家的瓜卤吸引得满村的孩子都往他家钻,他们干脆把瓜菜搬进了城里。后来,腌瓜菜的剩了老婆,有了钱的男人跟着别人跑了。女人就又回到了村里。
再回家时,仍吵着要吃瓜菜。就着那碗大麦粥,当年的清香爽口全然没有了。瓜菜仍是那个瓜菜,人却不是当年的了。而今的幸福和快乐,搀和了太多佐料,反而不容易找到原来的滋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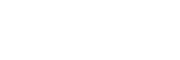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