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淮南周氏家谱》“原谱” 和“修订谱” 两大部分。 图片提供:周亚峰
东滨黄海的江苏省大丰市,是一个73万人口的县级市,辖区内14个乡镇中有12个乡镇的老百姓同说一种名为“本场话”的方言,且他们几乎都称自己的先人是古时候从苏州迁移到大丰来的。
这种说法与历史上著名的“洪武迁徙” 颇为相似。那么是不是真的有一批苏州人迁入大丰这回事呢? 600多年前的今日之大丰版图大半个泡在海水之中,西部地区的几个海边盐场时属杨州府兴化县地界,史书不可能顾及到这块人烟稀少的“边角料”上是否来过移民,丢开野史、民间传说、文学作品,现在要拿出真凭实据来很难。然而,近年来居住在该市草堰、白驹、西团等乡镇的几位周姓族人,却通过续修家谱,发现了一份很有说服力的民间证据。
一、 从周氏家谱原始记载看苏迁的真实性
这部名为《淮南周氏家谱》的“民间档案”,分为“原谱” 和“修订谱” 两大部分。原谱内容自元朝丁未年(1367)至民国八年(1919),修订谱内容自1919年至 2009年,系统地记录了“苏迁”之后642年间周氏家族历代生息繁衍概况。
修订后的《淮南周氏家谱》,至今仍保留的“原谱” 序跋可以见证苏迁历史的文字有多处:
“皇清乾隆岁甲子年”,署名“阳山后学乡进士选常州府儒学正堂徐鹔西白氏” 撰写的《淮南周氏家谱序》曰:“鼻祖良辅公苏迁堰上,本宋代濂溪先生后裔,流传迄今十数世于兹矣……”。
“皇清乾隆岁辛已年”,署名“阳山后学乡进士候选儒学正堂徐光斗” 撰写的《北堰周氏原其鼻祖》曰:“良辅公始自苏迁卜居此地继世序其谱牒,即以是为开创之宗厥……”。
“皇清乾隆二十七年”, 署名“兴化县文庠生、第十一世孙周彪” 撰写的《忆始祖》曰:“良辅公自姑苏徙居堰上也,世系濂溪公后裔,迄今十有五世于兹矣……”。
其后,在道光、咸丰以及民国年间写的几篇序跋也有与上述内容相同意思的话。
在《淮南周氏家谱》传记上,也清晰地记录了苏迁事实。譬如,苏迁到当年“草堰场”(今大丰市草堰镇)的周氏始祖良辅公名字后面,注了如下一段话:
第一世,良辅(字行,生殁俱失考),先世苏州人,居阊门外,由元时迁扬州府兴化县草堰场(苏州时称平江路,兴化时隶扬州路高邮府),为周氏第一世祖。
旧载,洪武初避张士诚乱,徙家堰上。(谨按:士诚以元至正丙申据苏,至丁未为明所克,越戊申始为明洪武元年。士诚之乱乃元末也,堰上之迁当为元时无疑)。
先世无考,娶何氏生二子,曰维贤、曰维善,葬本场天池之南。
1999年秋,笔者送孩子去苏州大学读书,依稀记得小时候看过的家谱曾说,先祖居苏州阊门外平江路,便想去凭吊一下平江路先人故址,结果大失所望:阊门一带竟然没有平江路!
2006年我在苏州市区购置了一套寓所,其后常在此小住。有一天,终于在苏州市区地图上找到了一条平江路,便兴冲冲地去实地踏看,不料此路竟在平门之南,约与阊门有十里之遥。这一查考曾令我对家谱的真实性产生疑窦。回大丰到老家查看原谱,方知元代的“平江路”并非指的是一条马路,而是一个行政区域的代称,如当今的杨州市其时称之为“扬州路”。 我恍然大悟:平江路即苏州也。先人没有错,是我自己小时候不识繁体字,长大后又不研究历史闹出的笑话。
今年清明,我回老家大龙乡扫墓,途经当年“草堰场”时询访了家谱中提及的那个“天池” 何在。乡间一位老者告知,旧时的天池,应在今草堰镇丰产村境内。
由此看来,如今居住在旧时草堰场四方的周氏族人之先祖良辅公,确是元末从苏州“徙家堰上”无疑。
二、从周氏家谱旧著来源看资料的可信性
《淮南周氏家谱》十五世系中有个周湘的名字,附注初名华玉,字芷卿,文庠生。谱中有一篇序言可见,这位清末秀才是《淮南周氏家谱》(原谱)的终修“主执”, 还有兴化县一位其晚辈的文庠生协助他完成的。我的祖父周永益是周湘的长孙,秀才爷主持修订的家谱,我家自然是有的。
初见家谱是1969年。是年夏天,我去大龙老家过暑假,有一天爷爷奶奶到生产队上工去了,我就翻箱倒柜地找铜板玩,无意中发现柜子里有一个青布包裹,抖开来一看,里面有好几本纸色发黄的线装本书。那时我刚小学毕业,虽识得封面上“淮南周氏家谱”几个字,但里面的繁体毛笔字却不认得,更不知此为何物。
正当我望着一大堆陌生的名字发呆时,爷爷放工回来了,他连忙神色慌张地把这些书收了起来。爷爷告诉我,这是家谱,不能随便乱翻。为什么不能呢?他说这里记着历代祖宗的名字,外姓人、女人不可触摸,即使子孙看谱,也应先洗手、烧香。我问他祖宗人呢,他说第一代祖宗是苏州人,早死了。
我还是不太理解爷爷为何那么紧张。后来,奶奶告诉了我其中的原因。
两年前,大队(村)里的红卫兵挨家逐户“破四旧”。 到我爷爷家后,没收了十几本古书还不走,非要爷爷交出属于“封资修”的家谱和帮人家看风水用的罗盘。无奈,爷爷只好忍痛把祖传的罗盘交给了他们。当这伙人执意还要搜查家谱时,读过私塾向来温文尔雅的爷爷终于忍不住发火了:“我是贫农,不是地主富农,我没有什么封资修家谱。我家相公(儿子)在县里做事是个共产党员,孙子也是红卫兵,你们不要欺人太甚!”
这一说有人相信了,但本生产队的红卫兵小将听大人说过周家确实有家谱,硬是赖着不肯走,爷爷吼道:“滚回去问问你们的爷爷奶奶,哪家以后用不着我这个老头子去看风水了再来搜查不迟!”听到这话几个小后生才识趣地走了,因为他们的长辈向来是很尊重眼前这位“风水先生”的。
1973年爷爷病故,我父亲决定拆掉房子,把孤独的奶奶带回去和我们一起生活。此时,“文革” 的余威尚在,父亲在大龙供销社当主任,他知道这年月家谱带在身边可能会惹来麻烦,便托他那贫农成分的二叔代为保管。十年后,我去二叔公家查看过家谱,他虽然没有文化,但视家谱为宝物,收藏保管得很好。
近几年续修家谱是洋心洼几位“本家” 发起的。2006年春天,我应邀去面谈相关事宜。他们待我很客气,说我的辈份比他们高,且想让我为他们即将衔接完稿的续修谱写个前言。我不敢贪功,没有答应。不过,我很关心书稿质量,问了先人名谱的根据。他们告诉我,一是在草堰镇寻访到一个古谱手抄本,二是复印了大龙乡一套原始古谱,两本内容完全一致。我放心了,因为他们说的大龙那套原谱,正是我二叔公家后人提供的。
事情有时巧得令人惊奇。我的大丰住所楼下一户也姓周,因不是同一个工作单位,彼此交流甚少,只知道他是草堰人。一个月前,我手中有了一本印好了的新老家谱合订本,与楼下邻居在楼道相遇时,两个同姓同宗人自然叙起了辈份。交谈中,他告诉我,草堰镇的那一套旧谱就是他家保管的。
说起护谱不易,本家兄弟也讲了一段曲折的经历:1969年秋末,草堰公社的造反派抄出周永茂家的“毒草”, 逼他戴上“高帽子”, 且用绳子扣起家谱挂在其胸前背后游街示众。当游街到烧饼店门口时,同姓族人周玉喜忽然向造反派队伍里扔了一串点燃的小鞭炮。在造反派慌乱之际,周永茂乘机逃脱了,这才有幸保住了这套祖传的宗谱。
从民国八年古谱终修算起,悠悠近百年,遥遥五代人,两个不同地方的周姓族人,历经战乱炮火、“文革”清洗,保管了两套完全吻合互为印证的家谱,令人不得不信服。
三、从周氏家谱人物传记看史实的关联性
虽然《淮南周氏家谱》的序跋里明确指出周家“苏迁”笫一人周良辅是苏州阊门人,同时也言之凿凿说他是宋代大儒周敦颐的后裔,还是让读过周敦颐《爱莲说》的人感到有些迷惑。资料显示,周敦颐(字茂叔,号濂溪)是湖南道州营道人,从未有过在江苏讲学、为官的记载,苏州何来其裔孙? 换言之,如果周良辅确实是周敦颐的后裔,而周敦颐与苏州或江苏没有半点瓜葛,那么周良辅其人是不是苏州人就值得质疑了。
近年来,笔者在苏州做事,有机会到苏州市图书馆、苏州大学图书馆查找资料,探究两者之间是否具有历史渊源。经过几个月的查询,现发现周敦颐与江苏有三点情结:
一是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元《至顺镇江志》卷十一中有“元(周敦颐死后皇帝宋宁宗赐封给他的谥号)公于天圣九年十五岁时,奉寡母郑氏从湖南老家投靠在镇江黄鹤山旁的舅父郑向,其母去世后即葬于镇江。”
二是报载最近浙江上虞发现的一套修于清光绪年间的山阴(今浙江绍兴)《天乐山周氏宗谱》上有“烂溪姑苏吴江一支” 的记载。而“山阴周氏始祖” 周澳是周敦颐九世,早年常在苏州一带经商。又据《扬子晚报》(2000年5月25日)报道:“根据苏州吴江《烂溪周氏宗谱》等史料,周澳之子周德在苏州一带经商,后因母亡父谪、居无定所而入赘吴江车溪,开族烂溪。”资料显示,在苏州吴江的这位周敦颐九世之后周德生于元至六十七年(1280),那么他成婚并可独立经商的年龄,应在1300年之后。大丰“草堰场” 的苏迁始祖周良辅是1367年离开苏州的,其间只相隔60多年,况且周良辅也不会未成年就一人来到苏北,那么其出身时间应该与周德成婚时间只相差四十年多年,其是周德之子、之孙都有可能。这种推论与皇清乾隆辛已年阳山后学乡进士儒学正堂徐光斗为《淮南周氏家谱》作序时写的《北堰周氏原其鼻祖》一文中“尔周氏也尔祖自苏迁,昔濂溪有九子(疑为“九世”之笔误---本文作者注)在苏尔,固濂溪之后裔也” 是比较吻合的。
三是据《湖湘文化名人衡阳辞典》,1037年周敦颐的舅父郑向任两浙转运使疏蒜山漕河时, 周子同母随迁润州丹徒县(今镇江市丹徒区)。那么,根据周敦颐出身时间推算,他来到镇江时是20岁。古时候20岁不结婚就算大龄青年了,因此周敦颐在镇江留下后代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综上分析,周敦颐虽是湖南人,但确与江苏有缘,尤其是其九世之子在苏州吴江成家立业并“开族烂溪”这段史实,与《淮南周氏家谱》中的有关记述不谋而合。周良辅是苏州人,元末移民到今大丰市草堰镇的史实毋庸置疑。
回过头来再看《淮南周氏家谱》,周良辅十五世周湘这个名字也是值得研究的。家谱记载,他起初并不叫这个名字,“初名华玉,字芷卿”, 后来才改为周湘。作为一名饱读诗书文章的秀才,《淮南周氏家谱》古谱的终修“主执”,他易名为湘,应当是有原因、有寓意的。笔者分析,有可能是寻根问祖毋忘自己是湘南道州人周敦颐后裔的意思,抑或也有自己作为道学、文学名人周敦颐之后,立志继承或告慰先人自己将沿袭周子文化衣钵的寓意。古时候的读书人是专攻中文和文史的,不像现在的学生被数理化、外国话弄得天晕地转,况且一百年之前的文史资料应该也比现在更靠近历史、更加广泛,因此有理由相信我的这位高祖对家史渊源的研究要比我深刻得多。
四、从周氏家谱“阊门徙迁”看移民的政策性
如今大丰有个奇怪现象:许多“本场人”不但说自己的祖先是苏迁过来的,而且说从苏州什么地方迁来的都很一致:阊门。这与《淮南周氏家谱》中“阊门徙堰” 的记载是吻合的。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这么多苏州阊门人迁居苏北呢?目前有两个“版本”: 一是“逃亡说”----为躲过朱元璋所部屠城而逃到今大丰市境内“草堰场” 来的。二是“发配 说”----被朱元璋政权强迫谴送到今大丰市境内“草堰场”来的。
“逃亡说” 很有市场。因为元朝末年朱元璋部队围城十个月之久,攻破苏州城池后发泄气愤,确实“大烧大杀,以致死者枕藉积骨如山”(见苏州市地方志办公室陈其弟《张士诚与苏州》一文)。如此暴行谁不害怕,有人逃往外地合理合情。因此,“逃亡说” 不但普通老百姓深信不疑,就连近年来几位修订家谱的周姓族人,尽管有先人的古谱摆在面前,一度也曾把第一世祖迁居草堰场的原因改写成与此相同的说法(在我看来,这是续修家谱的一个严重错误)。那么苏州人为什么偏偏逃到这海边古盐场草堰并在此定居呢?一位草堰藉史学研究者在其著作中这样写道(大意):当年在苏州称王的张士诚是草堰场人,逃亡在外的苏州人无处立足,只有对苏州有感情的“吴王” 故里的乡亲们愿意接纳他们,所以这批苏州人便在草堰场安家落户了。
“发配说” 有枝有叶。比较典型、最有说服力的是由草堰场(据说当时丁溪、刘庄、白驹等盐场均隶于草堰场)派生出来的“本场人”, 至今老老少少都把上厕所大小便称之为“解手”。 譬如,某人在上厕所,有人问起他去那里了,知情人往往会说:“去解手了。”那么“解手” 二字缘于何处呢?老辈人说,因为当年我们的祖先是被朱元璋派官兵用绳索一队队从苏州绑来的。路途遥远,难免要大小便,被捆绑的苏州人只好央求那如虎似狼的押送官兵:“官爷呀,我要小便了,求您行行好吧,帮我解开手。”有时有人要方便实在憋不住,也就来不及说那么多套话了,直接叫喊:“我要解手!”后来,苏迁人就习惯地把要大小便说成要“解手”, 代代相传,沿袭至今。这种把要大小便以“解手”为代名词的方言,是在大丰市境内的其他外地移民及其后代既听不懂也无法理解的。
传说终究是传说,当年的苏州人是不是被绑去海边盐场的,我没有找到史料根据,既不能肯定也不敢轻意否定。但我总觉得“逃亡说” 疑点甚多不合情理:一是敌军围困万千重,围城期间岂能放任这么多人逃脱?二是破城之后朱元璋大军随即“大烧大杀,以致死者枕藉积骨如山”, 大难过后还有逃跑的必要吗?三是东西南北中,偏偏逃大丰,哪里不比这海水煎盐的地方富饶?四是就算苏北草堰场是个好地方,围城时也有逃跑的机会,可苏州有胥门、金门、阊门、齐门、平门、娄门、葑门、南门、盘门等9门之多,为何只有阊门一带的市民信息灵通来了一大批人,其它“门” 的苏州市民却不见一个?五是这么庞大的一支阊门市民逃难队伍,谁有这样的组团能力?
因此我认为,苏迁应当是由朱元璋集团有计划、有组织的一次移民运动。丢开政治不论,打一个很不恰当的比方,其移民组织形式应与数百年后的“上山下乡运动” 差不多,即在城市里以区划片,然后集中这个片上“应该” 离开城市的人, 同时或分批送往外地某一区域统一安置。这样猜想,也许才能为这么多苏州阊门人同时移居草堰场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其实,当年被迁出的苏州人,去向并不止草堰场一个地方。据苏州市地方志办公室陈其弟所作《张士诚与苏州》一文说:“著名的‘洪武迁徙’,屡屡将苏城富户迁至京师(南京)、凤阳、苏北等地。”史料可见,阊门恰恰是当时苏城富户最集中的地方。这种以富户为移民对象的政策,为我们理解这么多阊门人同时迁出的原因又找到了一个根据。
事情发生在苏州,又是专门研究地方史的专家这么说的,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这一史实。可全国之大,偏偏把苏城富户分散到京师(南京)、凤阳、苏北这三个地方就值得研究了。
南京是朱元璋准备或己经做了首都的地方,凤阳是朱元璋的家乡,逼着“苏城富户”去这两个地方,用句时下比较时髦的话说,显然是利用职务之便以权谋私,强行“招商引资”,为发展朱元璋的“皇城经济”和“家乡经济”而制定的一项带有私心的倾斜性移民政策。
至于移民到苏北,决策者可能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苏北是朱元璋恨之入骨的老对手张士诚造反起家的老根据地,尤其草堰场是这个昔日冤家对头的出生地,把一批“苏城富户” 迁送过去也是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吗?恐怕朱元璋没有这个雅量。因此我分析,去苏北的这批人不仅是“苏城富户” 中的小户,而且肯定还是在抗击朱军攻城中的“积极分子”。把这些银两不是很多却又极不安分守己的人,送到贫穷落后的苏北,尤其是发配到这荒芜的海边盐场,显然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大局,兼惩罚这些异己分子而制定的又一项特殊政策。
五、从周氏家谱讳莫如深看徙迁的政治性
政治家决定的如此大规模移民运动,单纯地用“调整经济结构”去理解显然过于狭隘,必然有其政治原因。要完成移民任务,也必然要采取强硬的政治手段。
苏迁的政治原因,我想应该与当年朱元璋所部大兵压境,将苏州城攻打了十个月后才破城不无关系。试想,不算很大的一个苏州城池能支撑十个月之久,不足以证明当时军民一心同仇敌忾吗?朱元璋能不对苏州市民怀恨在心吗?而江浙一带既是鱼米之乡,又是商贾云集之地,在朝庭的财政收入中占有很大比重,是万万不能出乱子的。因比,朱元璋集团出于政治考虑,防止这些忠心耿耿的“吴王” 臣民怀旧作乱,弄坏他这只聚宝盆,故意把一些人遣散出去,恐怕才是苏迁的真正原因。
那时还没有做“思想政治工作”一说,即使有也不可能在一年半载内把这么多移民的思想工作做通。让那些在人称“天堂”姑苏小日子过滋润有味的富家子弟,心甘情愿地到贫穷落后的苏北躬耕农田,到海边盐场去吹海风住茅棚,谈何容易?
笔者注意到,周氏家谱中有“徙家堰上” 四个字。这“徙” 字,现在《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的注解就是“迁移”,没有别的意思。而比较古老的辞典则告诉我们,“徙” 还有一种解释:古代称流放的刑罚。如:徙边,就是流放有罪的人到边远地区。从元末开始记注的这套《淮南周氏家谱》年代久远,当属古代之作。感谢先人为我们留下这本珍贵的民间档案,留下这内容丰富的一个“徙” 字,让后人能够品味当年先人苏迁堰上时的辛酸苦辣和逼迫与无奈!
看来“捆绑押送” 虽是古老传说,未必就是空穴来风。
《淮南周氏家谱》这部民间历史档案,字里行间不仅透露出当年苏迁时白色恐怖,还向我们展示了苏迁之后的的政治气氛。这里,我们不妨对《淮南周氏家谱》中“旧载,洪武初避张士诚乱徙家堰上” 这句话作一点具体分析。
这部家谱首编于何年没有注明,我们现在看到的“原谱”仅是修订于清康熙四十年至民国八年的续修本。前不久,笔者与盐城市政协的一位文史委员分析研究后认为,《淮南周氏家谱》首次编纂当为明朝。一是明朝朱氏天下二百七十六年间,周氏家谱不可能没有记载,否则元末以来历代子孙及人物注记不会如此翔实。二是“旧载” 二字明确地告诉人们,编纂时间早于清朝康熙年间。三是是“洪武初” 三个字很含蓄,表明苏迁时朱元璋虽已气候大成,元朝事实上已不存在,但朱元璋尚未正式登基称帝,后来已为明朝臣民的编谱者,既不敢写苏迁时为元朝什么年号,又还没有具体的洪武年号可写,只好用“洪武初”(朱元璋即将当皇帝的时候)三个字模糊一下。这种写法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下, 应当是可以理解的。四是把苏迁原因说成是为“避张士诚乱”,显然既有悖历史也不合情理。“洪武初” 张士诚所部己被剿灭,何须再“避张士诚乱”?假如真的是为“避张士诚乱” 而逃亡的,怎会又偏偏投向张士诚“匪巢”(故乡)呢?已脱虎口,又主动走进狼窝,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只能理解为:因该谱始编于明朝,而明朝的“文字狱”又十分厉害,为免遭灾祸只能违心地这么写。否则,你实话实说,写“因当年在苏州城拥护支持吴王张士诚而受了连累,被朱重八这个王八蛋秋后算账,把我们流放到草堰场”,岂不是自找祸事准备灭门九族!
然而我们还是可以从“徙家堰上” 中这个“徙”字上,可以领悟到当初该谱首编者的难言之隐和隐晦手法。因为张士诚从未做过将苏州阊门人流放到自己家乡的事情啊,这不是暗指受张士诚牵连被朱元璋流放吗?“徙”字既可当迁移讲,又有流放的意思,用这个字既有应对白色恐怖的狡辩余地,也为后人了解实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可谓妙哉。
由此我们可以分析出当年苏迁移民时的政治气氛是多么恐怖。乃至事后在朱氏统治的年代里,人们还心有余悸不敢秉笔直书呢!
《淮南周氏家谱》可见,明朝年间周家有两代出过秀才,该谱修订过程中好几次是由进士把关并由他们作序跋的。如估计明朝首次编纂此谱者也是个进士,恐怕也不能说我得了狂想症。进士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通过最后一级考试者,是古代科举殿试及第者之称,没有理由怀疑他们把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一眼都能看穿的历史写错。春秋笔法,寓褒贬于曲折的文笔之中,非“大手笔”而不能为之!
六、从周氏家谱移民人口看总量的可能性
讨论当年苏迁到大丰的人口总量,得与当时到大丰“草堰场” 的苏迁人是否可能均来自阊门一地这个问题综合分析。我在前面已经说了“城市划区定人,集中迁移定居” 的观点,不再重复。现就人们容易忽视、疑惑的问题再谈三点看法。
首先, 现在说“本场话” 方言的人,不一定都是苏迁人的后代。因为人们所说的“苏迁”, 当指元末明初的“洪武迁徙”, 其实在此之前今日大丰市境西部地区应当是有一定人口数量的。何以见得?当年盐民张士诚从草堰盐场起兵反元,如果没有一定数量的家乡子弟兵作为中坚力量,跟随其浴血奋战并拼死守卫,其不可能打下了一块南至浙江绍兴、北至山东济宁的疆土,更不可能割据称王十多年之久。六百多年来,苏迁之前正宗的本场人也在不断繁衍,不过今天他们与同化了的苏迁人后代同说一种方言,有些没文化或没有家族意识的人压根儿就不知祖宗是谁,只好跟在别人后面人云亦云,这就使得谁是真正的苏迁人后代,谁是正宗的本场人后代难以区分了。
其次,应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六百年前的阊门。现在的苏州城似乎很大,外地人很难在偌大的苏州注意到阊门这个小地方。其实苏州城的“盘子”是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才做大的。东辟新加坡工业园区,西扩高新经济开发区,南吞吴县城,北建相城区,能不大吗?实地察看你会发现,阊门即现在“石路” 一带,是苏州除观前街之外的另一个商业中心。有资料介绍,明清时期这一带曾经是全中国最繁盛的商业街区。包括城外呈放射状的南濠街(今南浩街)、上塘街和山塘街,以及城内的阊门大街(今西中市)。与这些街道平行,又有外城河、内城河、上塘河(京杭大运河古河道)、山塘河(通往虎丘)分别从五个方向汇聚于此。清代乾隆年间的名画《姑苏繁华图》,《盛世滋生图》都表现了当时阊门至枫桥的十里长街万商云集的盛况。当时这里各种店铺多达数万家,各行各业应有尽有,各省会馆纷列其间。我不是史学家,难以论证当年阊门的繁华景象,还是让我们用人所共知的明代著名书画家、文学家唐寅写的一首《阊门即事》诗来品味它的历史辉煌吧:
世间乐土在吴中,中有阊门更擅雄。
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
五更市卖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
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道画难工。
由此可以想象六百多年前阊门作为苏州商业中心有多么繁华,人口多么密集,从这里疏散一批人并不奇怪,也不会造成多大影响。
第三,应用人口发展的眼光来考量当年苏迁人数。对苏迁人全来自阊门一地持怀疑态度的人说:“阊门我去过的,不过是苏州的一个小旮旯。如果迁出那么多人到苏北,还不家家走空户户关门啊!”看了前面对阊门过去的叙述,这不应该再是个问题了。我们再来看《淮南周氏家谱》记载的周氏苏迁到草堰场的人数:只有周良辅一个人,既无父母也无兄弟姐妹。由此可见当时被移民的对象明显具有“抽壮丁” 的痕迹,这与史学家所称“两丁抽一,五丁抽二”的说法是一致的。因此,我作一个大胆的猜想:当年苏迁到草堰场的苏州阊门人至多二百人。何以见得呢?据苏迁之后120年的《弘治运司志》记载,今日大丰西部的几个盐场总人口也只有7679人。这是正宗的本场人和苏迁人共同繁衍了五六代人的数字,可想苏迁时又能有几百人呢?再看《淮南周氏家谱》当初记录的周氏只有一个人(周良辅),事隔642年传了二十多世,现今谱上有名的健在小辈有一万多人,这还不包括盐城、东台、兴化(部分),以及大丰市的刘庄、小海、新团等乡镇未能统计登册的同根同源周姓族人。那么,如果把元末明初来的“二百个苏迁人”的后代全统计起来,至少也在三百万人口以上。就算苏迁人的后代向草堰场四个不同的方向平均分散,那么兴化、东台、盐城、大丰,平均每县也有六七十万人。这样推算的话,可能估计当初来了200个“苏迁人”,还有点过于乐观!
因此,不要看今日大丰满眼都是自称苏迁人后代的本场人,其实当初苏迁也许就那么一二百个“种子”, 既不会影响阊门经济运转、人口繁衍,也不会增加草堰场各分场多大负担。况且,有相当一部分“本场人”是正宗的本场人,他们并不是苏迁人的后代。
阅读《淮南周氏家谱》,笔者感到它既是一部年代久远的家族宗谱,也是一份非常珍贵的民间历史档案。透过这部家谱,我们可以穿越历史时空,感知、领悟出六百多年前从苏州移居到苏北古盐场草堰的那批先民们,迁居的时间、原因、对象、过程,并能大致判断出当时移居草堰场的人数,这对研究苏迁移民史、人口发展史、风土人情,应当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
周亚峰,男,1957年生,江苏大丰市人。1974年参加工作,做过基层供销社职员、市供销合作总社宣传干部、企业工会主席。在报刊上发表新闻、散文、评论、论文作品300多篇,曾获人民日报征文竞赛一等奖、三等奖各一次,著有《我身边的故事》(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
严正声明:本文为本站特约稿件,若需转载,请与大丰之声或作者本人取得联系013615169928,经同意后方可转载。谢谢合作,违者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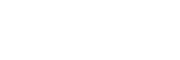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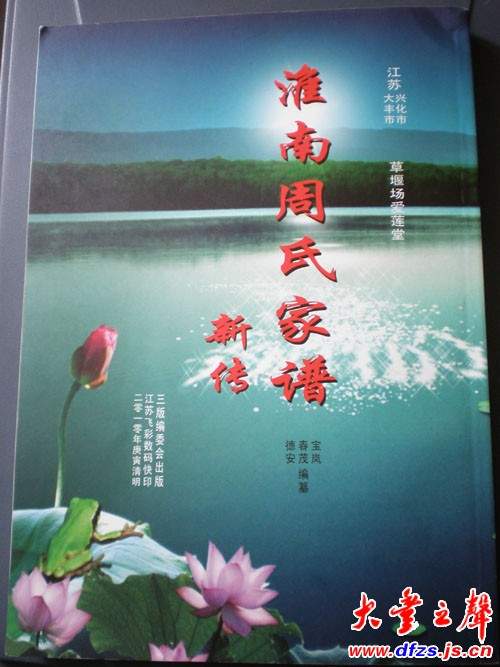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