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个春日。
太阳眨着惺忪的目光,风儿有一搭没一搭地吹着,全没了往日的神气。不知是谁打了个长长的哈欠,随即传染病般迅速蔓延。望着一屋子萎靡,先生有点无措。
“离山十里, 薪在家里; 离山一里, 薪在山里”。突然,有歌声脆脆地传来,似一根无形的绳子,将先生牵出门外。
门外一稚子,背着柴火,拿着砍刀。
“是你唱的?”先生疑惑地问。
“是的,先生。”
“你叫什么名字?”
“先生,我叫朱恕。”
“在哪念书?”
“我,我……”童子窘迫起来。
朱恕自幼丧父,母亲又沉疴在身,为支撑家庭,小小朱恕,五六岁就当起樵夫,跟大人一起外出砍柴。由于力气小,挣来的钱不够家用,朱恕便将好一点的饭食留给母亲,自己悄悄地吃糠咽菜。至于上学读书,那是想都不敢想了。
“贫寒出栋梁,逆境出才子”。先生教了大半辈子书,还没碰到如此聪颖、孝顺且又彬彬有礼的孩子,遂当即决定,免费收朱恕为学生。朱恕闻言,“扑通”一声跪了下去,朝先生磕了三个响头。
先生将朱恕带到众生面前,欣喜地对大家说:他叫朱恕,那首樵歌就是他唱的。歌虽简单,却蕴含着深刻的哲理。你们应该知道,道理处处有,求则得之,舍则失之也。
先生就是王艮,朱恕能够饱读诗书,成为明代“泰州学派”的主要成员,王艮起了很大作用。
求学期间,朱恕一日三餐,概以窝头充饥。寒冬腊月,仍穿着单薄的衣裤。同学不忍,欲以银两赠与。朱恕谢绝:你不是爱我,而是害我。我若因之贪图享乐,岂不断送一生?同学又悄悄赠与寒衣,朱恕还是坚辞:此衣非我所有,若穿上,岂不是自欺欺人?
有人劝说:你先把东西收下,日后报答就是,你如此不仅害苦了自己,还得罪了人家,何必?
朱恕正言,日后如何谁能预知?我不能凭空欠人人情。
这便是少年朱恕:洁身自好、笃志为人。王艮十分得意,逢人就说:我这个学生,将来一定大有可为!
王艮的话只对了一半,毁掉另一半的,竟是朱恕自己。
州府有个学使,名叫胡植,仗着朝中有人,贪赃枉法,胡作非为。可笑的是,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人,也想博取好儒雅名。朱恕此时已是声名显赫的理学大师,胡植暗忖,倘能同他扯上关系,定能提升自己的身价,于是躬下身子前去拜访。
官员亲临寒门,这在一般人看来,乃求都求不到的好事。可朱恕最最痛恨的就是倚强凌弱、装腔作势之人,见到胡植,竟然连门都不让人家进。盛怒之下,胡植当即动用权力,命令朱恕去服劳役。朱恕也不争辩,剥下长衫,退去鞋袜,义无反顾地加入劳工行列。同学点拨:认个错吧,或许还有挽回的机会。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朱恕随口吟道:明暗若违还伪学,鬼神如在是真修。同学顿足:真正的书呆子了!
朱恕以自己的人格魅力,赢得了民众的敬重,也得罪了一些权贵。他的恩师王艮,一直想为他谋个合适的差事,好让他学有所用。上面传言,只要他乖巧,一切好说。老师大喜,忙差人传与朱恕。朱恕却说:吾生平无他好,唯一“信”耳。
因了这个“信”,朱恕清当了一辈子布衣,清心寡欲,安之若素,其高风亮节,与戴家窑韩贞吾齐名,一同被冠以“东海贤人”。二人的著作,也被后人辑为《朱乐斋、韩贞吾两先生遗集》,流传于世。
朱恕生前没能发达,死后却红火起来。里人鉴于他生平清白,刚正不阿,取“光信”为他的字,给他树碑立传。尚书耿定白,一篇洋洋洒洒的《陶樵传》,将朱恕的为人和学识,写得情真意切、催人泪下。
何谓“陶樵”?是否指陶瓷做成的东西,好看却极易碎,就如朱恕为人,学富五车,却不能保护自己,不得而知。朱恕的墓地,经后人多次修缮,已成漂亮的园林。1987年,大丰县人民政府为表彰他的遗德,还将其墓地定为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紧接着,草堰镇政府又乘势而上,把朱恕的墓地改建成“朱恕园”。
如今的朱恕园,松柏环绕,四季常青。登高俯视,绿树红花,小桥流水。穷困一生的朱恕,终于有了自己的洋房和花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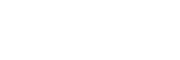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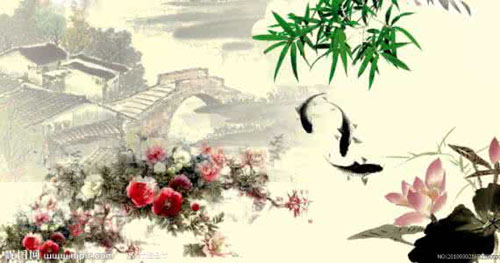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