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4点,天还没透出一丝光,远处几声鸡鸣撕开沉沉的夜色。薛太和轻轻推开宿舍门,紧了紧洗得发白的中山装,从墙角推出自行车。轮胎的气是昨晚临睡前打好的,车链条上了油。这天,他要去大桥公社。
车轮碾在砂石路上,沙沙的声响在寂静的凌晨格外清晰。那时的公路不像现在黑色柏油路面,都是砂石铺成,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没有整夜亮着的路灯,只有东方天际一抹若有若无的鱼肚白,勉强勾勒出两旁刺槐树的影子。风从盐碱滩上吹来,带着潮湿的凉意。从大丰县城出发,经裕华,过通商,奔草庙,再到目的地大桥,九十多里路,全靠脚蹬。
骑到裕华时,天色青灰,早起拾粪的老汉佝偻着腰,在路边的田埂上移动,看见他,直起身眯眼打量。薛太和点点头,算是打过招呼,车轮未停。砂石在轮下细细地呻吟,有时崩起一颗,打在挡泥板上,“啪”一声脆响。汗水渐渐沁湿了他的后背,额发也贴在了皮肤上。过通商时,天已大亮,公社大院里的广播开始播送新闻,嘹亮的声音在空旷的田野上飘荡。他看了看手表,加了把劲儿。
到大桥公社地界,已经是早上8点,太阳已升得老高,他径直把车骑到安排好的生产队田头,支好车,脱下外衣,卷起裤腿,就下了田。旁边正在劳动的社员们直起腰,目光齐刷刷地落在这个突然出现的、干部模样的人身上。
一个面色黝黑的老把式先开了口,嗓音沙哑却洪亮:“喂,这位同志,你是上面来的干部吧?”薛太和笑着点头,手里没停,跟着社员干活。老把式却不客气,指着太阳:“你看看日头,都啥时辰了?太阳都有一竿子高了,我们天一亮就下地,汗珠子摔八瓣干到现在快两小时了。你这会儿才来,点个卯、做个样子?如果我们都像你这样上工,咱年底分红怕是真要喝西北风了!”话像带着刺,砸在田垄上。周围的社员有的低头偷笑,有的面无表情地看着。薛太和手上的动作顿了一下,脸上那点笑容收敛了,他抬起头,很认真地看着老把式,说:“您批评得对,是我来得晚了,我检讨。”说完,埋下头,更用力地干起来。

日头爬到头顶,公社通讯员小跑着来请他去吃饭。公社食堂里,桌上摆着一碗饭,一碟韭菜炒鸡蛋,一碟青椒肉丝,还有一碗飘着几片菜叶的清汤。这在当时,尤其是在乡下,已是难得的“招待”。薛太和吃好饭,从口袋里掏出饭钱和几两粮票,数好,压在碗底。“规定就是规定,不能坏。”他语气平和,却不容置疑。吃完饭,他又回到田里。
下午的活更累,薛太和依然跟社员同进同出,劳动进度并不落下风。休息的间隙,刚才那位老把式凑过来,递过一瓢井水,目光却瞟向田埂上那辆自行车:“薛书记,你那脚踏车,好家伙,崭新!咱全生产队,百十户人家,摸不出一辆自行车票。你这车……是咋来的?敢不敢说说?”话里带着试探,也有些许不服。旁边有人拽老把式的衣角,老把式一梗脖子:“怕啥?问问不行?”薛太和接过水瓢,咕咚咕咚喝完,用袖子抹了把嘴,笑了笑,说:“车是组织上配的,为了方便工作。您要是觉得不妥,回头我们可以讨论。”他答得坦荡,眼神清亮,倒让老把式一时接不上话,咕哝两句,转身走开了。
收工的哨音响起时,西天已烧起晚霞。薛太和拖着酸痛的身子,在公社门口的水缸边洗净手脚,推上自行车。公社干部挽留他住下,他摆摆手:“明天县里还有会,得赶回去。”
回程的路,似乎比来时更长。疲惫像潮水般涌上来,眼皮发沉。骑到草庙北面一段坑洼特别多的路上时,“咔哒”一声,链条突然滑脱,卷曲着垂下来,像条死去的黑蛇。他下车,蹲在路边,捡了根硬实的树枝,一点点去勾、去挑,试图把链条搭回齿轮。油污沾满了手指,怎么也弄不干净。弄了好一会儿,总算挂上了,蹬起来,链条嘎吱嘎吱响,总怕它再掉。

屋漏偏逢连夜雨。离庆生渡口还有几里地,车胎又被路边刺槐树上尖锐的硬刺扎了个正着,“嗤”的一声长响,车头立刻沉了下去。这回,是彻底没法骑了。四下望去,暮色四合,旷野茫茫,只有风吹过芦苇的沙沙声。没有修车铺,甚至连个过路人也无。他叹了口气,只能推着这辆“瘸了腿”的伙伴,一步一步,朝着渡口方向跋涉。
当天夜晚,大丰县委大院一群人已经焦急万分。马县长背着手,在办公室窗前踱来踱去,不住地看表。早已过了薛书记该回来的时间,却一点消息都没有。“不会出什么事吧?”这个念头让他坐立不安。那时候,没有手机、传呼机,乡镇以下,电话更是稀罕物。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找。他不再犹豫,叫上司机,发动了院里那辆老旧的绿色吉普车,沿着大丰通往大桥的砂石路,一头扎进浓稠的夜色里。车灯劈开黑暗,像两柄焦急的剑,扫过空旷的原野。马县长睁大眼睛,紧盯着路边每一个像人影的轮廓。
吉普车颠簸着开到庆生渡口时,已是深夜十二点。终于在渡口对岸找到了薛书记!他正抱着膝盖,坐在渡口边的石墩上休息,身旁是那辆轮胎被轧破的自行车。
马县长抢步上前,一把抓住他的胳膊,上下打量,声音竟有些发颤:“老薛!你可把人急死了!怎么样,没事吧?”薛太和的脸上沾着尘土,手上还有黑乎乎的油污,衣服也皱巴巴的,模样颇为狼狈。但他看到同事,眼睛却弯了起来,露出熟悉的、略带歉意的笑容:“没事,没事,就是车不争气,耽误了。害你们跑这么远,这么晚……”话没说完,就被马县长打断:“人平安就好,平安比什么都好!”
这段往事,像一颗被岁月磨圆的石子,沉在亲历者的记忆河底。精神矍铄的老人家侃侃而谈,我们几个听众却无比震惊。
听老人家笑着讲这段往事,我的脑海里随即呈现出一幅幅画面,画里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有掉链子的自行车、钉刺槐树刺扎破的轮胎、农民直白的抱怨、掏钱交伙食费、深夜寻人的吉普车……这些细节如此平凡,甚至有些“窘迫”,这是我们大丰一个老县委书记的“人在囧途”,却让我无限怀念。
我怀念的,并非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而是那种“在一起”的状态。干部与群众,坐在同一条田埂上喝一瓢水,面对同样的尘土与风雨。那时的隔阂,是物理距离的遥远、通讯的不便,但心可能贴得很近——近到可以当面锣对面鼓地批评,近到你的狼狈我能看见,我的焦灼你能体会。那种联系,是用脚板丈量出来的,用汗水搅拌在一起的,因而也带着泥土的厚重与生命的温度。
薛太和们的“糗事”,像一面镜子,让我们反思:路越走越“快”的时代,那些慢的、笨的、甚至有些狼狈的“行走”,或许才真正通向人心深处。
(注:文中部分情节做了修改,图片为AI生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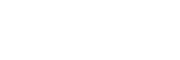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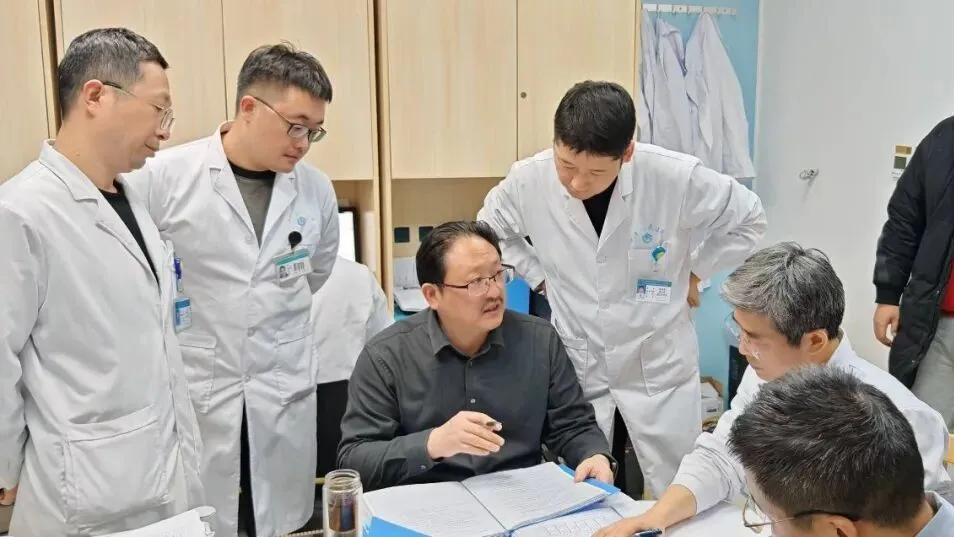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