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亲的双手大于常人,与矮小的身材很不对称。打记事后,常帮她挑扎在手上的草刺,总因大手而好奇。参军后,回原龙堤镇龙堤村的老家探家,偶尔帮母亲修剪指甲和老茧,握住比自己还粗大的手,大手始终困扰着我……
15年前的那个冬月,午饭后准备小憩,突然手机响起。在老家那头,侄子带着哭腔:“八叔,奶奶刚刚走了,你赶紧回来……”
我头脑“嗡”了一下,跳下床翻出身份证和银行卡,从四楼冲了下去。旁边的银行取了些钱,向开往长途车站的公交站台跑去。在回老家盐城的大巴车上,母亲的大手像放电影似的不停地在眼前浮现……
母亲的履历写满苦难与辛酸
上个世纪20年代后期,祖籍便仓明亮村的母亲还没完全记事,30多岁的外公因抱病英年早逝。国难当头兵荒马乱,是外婆带着母亲和她的兄妹流离失所,边做点小生意、边四处流浪活了下来。我如今工作生活的姑苏城,就曾留下过母亲年幼时的足迹。
不到20岁那年,由上代老亲引荐,母亲嫁给了大2岁的父亲,一生生养了我们兄弟八人。
兄弟八人中我最小,见证母亲的苦难是她人生后半程的事了,前半生更苦难、最煎熬的经历,多是听到的故事。
童年和少年的母亲,大多是寄人篱下并伴随泪水中度过。特殊的家庭环境和生育众多孩子的经历,注定了母亲一生与苦难为伍,与辛酸相伴,与泪水共生。
在国家困难,民不聊生年代,母亲用柔弱的双手支撑着家庭。父亲主外,她主内,天衣无缝地配合着,将兄弟八人抚养成人,其艰辛与不易,笔墨难尽其叙。
战争年代,父亲曾为革命队伍转送战备物资,做后勤保障,常年奔波在外。母亲常用锅底灰把脸抹黑,带着2个年幼的哥哥逃避战乱和土匪恶霸的侵扰。全家难得相聚,母亲总宽慰父亲放心家中,只要把公家的事情做好了,国家解放了,老百姓才有好日子过。
当年,身为长子的父亲,分家就得到一床破旧的被子和十多亩盐碱荒地。一家五口父亲挑着几十斤粮食和一个哥哥配成的小担子,母亲则怀抱和手搀两个哥,从步风的幸福村,来到几公里外龙堤车滩口西边叫“墩子头”附近安家,前2年租住在别人家,后来搭个草棚有了属于自己的家,这里成了几代人的衣胞地。
在当地,我们这个十里八乡出了名的大家族,与父母年龄相仿的老人,对二老的苦难了如指掌,在他们眼里,父母以何等的毅力把八个儿子拉扯大。特别是母亲,连个做针线活的帮手都没有,光一家的缝缝补补,是怎么的艰辛啊……
早年,大人曾有“换亲”计划,准备以我家男孩跟别人家换个女孩,替母亲分摊针线活,几次基本促成后,都因母亲阻挠而不了了之。
我记事时,家中就有一台木制的纺纱织布设备。母亲说,当年她白天参加集体劳动,靠早晚空隙,用这个简易的设备纺纱织布。织好的粗布再用植物的茎叶熬成汁染上颜色,最后一针一线地缝制成衣服。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新衣服的,旧的还要缝缝补补多少回,穿过多少人,经历多少四季轮回,才有新的更替。
我的印象中,除非躺在病床上,几乎没见过母亲休息的模样。清晨历来是她打开大门,晚上最后插上门闩。小时候我常想,母亲是不是没有睡眠呀?
床顶篷上常年被母亲系着一根铁丝,在与脸差不多高的位置,挂着一盏自制的煤油灯,那便成了每天早晚做针线活的操作台。
上中学前,我一直睡在母亲里侧,睡前,母亲总先准备若干根针,叫我穿好线后备用。无论夜里担心尿床叫我小解,还是早晨自然醒,母亲的小灯始终亮着,而头发和眉毛不知被烧焦多少次。后来,年纪上升的母亲戴上了老花镜,在微弱的灯光下她的脸渐显苍老,腰也慢慢地佝偻起来……
家里的衣柜中,长期存着一二十双手纳成的鞋底。这是母亲平时见缝插针,一针一线纳成的,每到夏天她都搬出来防潮曝伏。母亲说等哪天老了,鞋子做不动了,这些也能应付过几年呢!
母亲田间劳作没有日夜之分,白天有天然光线,晚上则以马灯代替。她常白天就把马灯带到地里,天黑后点亮再做上几个钟头活计。实在累得支撑不住了,母亲甚至坐在地里赶手中的活,从不见抬头……
每到秋冬季节,母亲就带领大家将农作物秸秆和沟坎河堤上的杂草,收割后集中运到家中。由于人口多,喂养的牲口更多,燃料消耗总数倍于别人家,每年都要储备几个小山似的草垛。推草垛时,多为身材娇小的母亲站在高处,将草一层一层地压实,最后在比屋还高的顶端,巧妙地做收边和防漏处理。此时,瘦弱的母亲成了全家的制高点……
冬季的时候,母亲的手裂开的口子像张着的小嘴,不时往外渗血……更常被树草的刺扎伤,经常发炎长成刺窝钻心地痛。自小,母亲常叫我用针帮她挑刺。 起初,我不敢下针,她便“下不得辣心,当不成医家”来鼓励我。于是,我咬着牙,颤抖地用针把扎刺旁边的肉慢慢挖开,再轻轻地挑出刺来。有时为挑一根深刺,手被挖得鲜血淋淋……
母亲用双手托举希望,迎接生命
日子再艰难总得往前过。母亲总是苦水往肚里咽,把温暖和希望留给别人。
“大跃进”吃食堂时期,八兄弟五人已出世,大的哥哥上中学,小的一二岁嗷嗷待哺。集体食堂打回来的饭粥根本填不饱肚子。母亲总让哥哥们先吃,而自己就以南瓜、萝卜、山芋甚至野菜充饥。她说,孩子们长身体更要赶路上学,饿着肚子不行,只有吃饱了才能学习好,才有改变贫困命运的机会……
我的印象中,吃顿米饭只有过年,或者重要的节气才有运气。嫂子们坐月子,或偶尔来亲戚也能闻到米饭的香味,但我们没资格吃,是母亲在锅旁边专为特殊成员插点米饭,更监视着不准我们碰。
也曾有过一次饱餐米饭的经历,那年,家门口集体的水稻收割完,母亲动员我们捡拾稻穗,答应奖赏一顿米饭。没成家的几个兄弟用一早一晚的工夫,捡拾了可能超过一餐米饭的稻穗,被奖了一顿纯米饭。那个香啊,一生都难忘……
封建习俗也影响着母亲,平时吃饭、特别是来了客人,从不见她占桌边。大多坐在灶膛前,更多的时候捧着饭碗,在附近的田边转,或在猪圈门口看看自己饲喂的猪家族们。有时饭还没吃完,她就将碗放到一边开始做事情了。
母亲的鲜血曾染红了年糕。那年春节前在别人家舂年糕粉,父亲和哥哥们在后面轮流踩臼杵,通过前边的榔头舂粹石臼里的米。母亲利用榔头上下起落的间隙,翻拨石臼里的米,并用罗筛筛出米粉。从夜晚到凌晨,由于疲劳母亲反应稍有迟缓,与上下起落的榔头没配合好。瞬间,沉重的榔头插到母亲正欲捞米粉的右手。殷红的鲜血迅即喷射而出,母亲当即昏了过去……
幸好是擦伤,然而,起关键作用的右手食指受伤变形,永久的丧失了做针线活的功能。事后,母亲不知流了多少次泪,不是因为疼痛,而是担心以后一家的针线活怎么办?
我们家历来六畜兴旺,尤以饲养老母猪闻名,最多的时候甚至二、三头,直到我参军后也没间断。而鸡、鸭、山羊、兔子等也曾规模不小,猫、狗更从没缺过。我爱人生儿子期间,家中两头母猪几乎同时生产,紧接着老山羊到了预产期,就连家猫也赶在那几天“凑热闹”,老母鸡孵的小鸡又先后出壳。那段时间,母亲整天合不拢嘴,逢人便说,看我家多兴旺啊,几天多了几十条生命……
老母猪一年产仔两次,母亲成无一例外的“接生婆”。即将生产的母猪常疼得直转。母亲到圈里后便乖巧起来了,她用手在母猪的肚子上挠几下,再喊两声 “睡下、睡下”,老母猪就配合地躺下,接着一个个小生命从屁股滑了出来……
母亲跟喂养的小动物似乎有专门的“交流”途径,平时到地里干活小家伙们总前呼后拥。关在圈里的猪家族们一听到母亲的声音,立即竖起大耳朵,嗷、嗷、嗷地叫着等吃的。母亲常说:“只要对它们好了,它们就会给家里带财,当年,主要靠这些宝贝挺过贫困,要不真难养活你们,更供不起上学、找媳妇成家……”
母亲以已之力传递温情,孕育家风
目不识丁的母亲,不懂深奥的处世道理,但她清楚“予人玫瑰,手留余香”这个理。老人一辈子有抽烟的习惯,但凡家中来客,不管对方抽烟与否,给来人递支香烟似乎成了她的惯性反应。偶尔也有客人递烟给她的,母亲就来一句:“哪有来客不烧茶,倒找一支烟的?”说着,忙把手中的烟往来客手上塞,直到对方接了才放心。
母亲提前几个月将几只老母鸡下的蛋,攒起来留给我爱人“坐月子”吃,是家人后来说起来的。得知又添孙子,老人家兴奋得几夜没合眼,每天争着要步行到二三十里的街上探望,终因不认识路被家人拦下。于是捎口信要我爱人早些出院让她伺候,理由是她自己生过孩子多,料理过的“月婆子”也多有经验。
母亲很注重规矩意识,对晚辈要求严格,从不准我们做事越线。
部队纪律的严明,母亲似乎比我还清楚,每次探亲她都打听好我休假的时间,算好归程的日期,假期结束前几天“驱逐令”就来了,要我早点处理好手头的事准备归队。她的意图更一语道破,你既然吃了部队的饭,就是公家的人,军队纪律如山,军令如刀,千万不可逾假不归,否则会受军令处罚。有几回跟领导打好招呼能宽松几天假期,母亲都没答应。她说:“你多休息了,战友就要增加工作量,如果人家这样,你肯定也不乐意”。说到最后再来句:“宝宝,就正常归队吧!”
老人家更提前为我的归队忙碌,把手上拎的,后背背的各种土特产准备妥当,一点不“体谅”我几番倒车、行李太重甚至罚款的“苦衷”。她说:“是战友们替你把任务完成了你才有机会探家,归队了就该带些家乡的味道犒劳战友。”
十多年前,苦难且劳碌了一生的母亲,终在近80岁高龄因二度中风彻底倒下,再也没能站立起来。即便临终前瘫痪卧床的几年间,母亲的手也不曾闲过,床边始终放根小竹子,发现钻进家中偷食捣乱的小动物,就右手抓住竹子的一端,颤抖地举在空中挥动驱赶,直至淘气的小家伙退到门外,她手才停下来……
走出盐城长途车站,天色已晚,我拦了辆出租车往大丰老家赶。到了龙堤小街往西,漆黑的夜晚,我一边给不熟路况的司机导航引路,一边使劲地盯着老家的方向,幻想消息也许是误传,甚至回到家再喊声妈妈,能和老人说说话。然而,随着老远反射过来强烈的灯光,事实证明81岁的老母亲真的离开我了……
下车后,我从大家让出的道中冲向客厅,母亲已静静地躺在灵床上,再也没了往日迎到我慈祥的笑容。我“扑通”一声跪到地上,轻轻地抚摸着母亲的脸庞,早没了余温。再将手伸进寿衣的袖口,握着冰冷尚未完全僵硬的大手久久没有松开。此刻,我才真正读懂这双大手,是母亲一生辛勤劳碌所至,那道道沟壑写的都是苦难。它似老树盘亘的根须,将毕生精力和无私的爱奉献给了子孙后代,倾其所有温润身边的人,唯独没有自己……
母亲那双粗糙而硕大的手,在我心中永远是世界上最美的手!
作者简介:周秀桐,江苏盐城大丰龙堤人,现供职于苏州市某区级机关,中国散文学会会员。80年代中期参军,曾长期服役于新疆军区空军、新疆军区机关,2003年调入苏州军分区,2007年转业,中校军衔。在部队多年从事新闻工作,被《新疆日报》社、《新疆经济报》社等媒体聘任驻部队记者数年,在各类媒体发表作品超过1500篇,数十次获得军地新闻工作先进荣誉,四次荣立个人三等功。目前,主要涉及随感而发的文学类作品,写生活、写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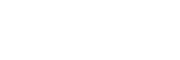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