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阳中学搬走了,在距老校址数十里外的大丰港,重建了一个 “新的南阳中学”。我听到这个消息,失落的感觉不啻于拆了自家祖屋。
南阳中学创建于1952年,因校址设在南阳公社境内而得名。这里是民国初年围海造田后的垦植区,每一块田地都呈面积相等的长方形,南阳中学占地四块,校区面积80亩。
昔日的南中,曾是我县仅有的三所完中之一,四面壕河碧水环绕,校园内布局精巧,教学区、生活区、运动场井然有序。南中校园很美。校门两边的门房,青砖红瓦造形别致。青砖路面宽阔平坦通往校内,两旁修剪整齐的冬青树和高大的翠柏郁郁葱葱一路相随。办公用房和教室,都是呈民国建筑风格的带走廊大平房,青砖红瓦典雅气派。校园内绿树成荫书声琅琅,沟河池塘碧波荡漾。那份人文景观,别说当年在全县各学校中独树一帜,即便以当下眼光也具有庄园式美感。
链接:周亚峰文集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在这里读过几年书,师长们的音容笑貌,至今记忆犹新。
校园外不远处有间小茅屋,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闲居在这里。他是一位和蔼而健谈的长者,我每次去拜访他,他总是一边把弄着家前屋后的庄稼,一边意味深长地给我讲些历史故事。他,是靠边站的老校长陈耀然,据说六十年代曾任地区行署监委书记,月工资高达八十元零五角。
我读初二时,学校来了一位年轻女教师,教我们政治课。有一次上课我在信笔涂鸦,邻座的同学打小报告说我在写诗。老师笑盈盈走过来,说想欣赏我的诗作。我吓得慌忙把那纸撕成碎片,因为我写的是一首编排某老师的打油诗。她叫魏翠萍,南京人,北京大学政治系毕业。
化学老师王树森是个有趣的人。他戴着一副近视眼镜,胡子刮得铁青,衣着非常讲究,颇有绅士风度。王老师讲课总是那么从容不迫,但他只会讲阿拉上海话,且声音尖细,真可谓余音绕梁,不时引来同学们的笑声。他课讲得很好,据说是名牌大学毕业的,上海一资本家的女婿。
语文老师杨德成的课,我是最爱听的。他是扬州人,从一所师范院校调来的。他讲课真似成竹在胸,从来不看讲义,谈古论今广引博证,诗词歌赋如数家珍,海阔天空潜移默化。他打开话匣,时而声音低得须让人竖耳静听,时而语调高亢且配以有力的手势,仿佛要将教室屋顶掀翻。

那时的南阳中学教师队伍,没有“近亲繁殖”,大多是上海南京来支教的客藉教师,也有从北大南大毕业分配过来的,有的是师范院校撤销后划过来的,有的是受运动牵连从上边发配下来的,就连那个成天扫场地浇花圃的刘裕,也是家住南京城的老牌大学生,真是藏龙卧虎呢。
要问当年南中师资力量有多强,数年后“金子发光”可见一斑。老校长重新出山,成为县政协副主席。年轻教师魏翠萍,破格提拔为分管文教的副县长。老学究王同书去了省社科院,当上文史研究员。受运动影响的施恒祥老师,担任县广电局局长。美术老师王荫华,成了著名漫画家。杨德成、王树森、王益民、孙学观、包庆源等当时的普遍教师,都成了县城重点学校的领导人。
老实说,虽然我的老师们都是八方英才,但我在学校里算不上优秀学生。那年月盛行读书无用论,我是实用主义者,只注重语文和政治,认定将来走上社会这两门功课有用处,而听数理化课,我多半只是欣赏老师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多年后,不少同学见到我,印象也仅仅是“经常在学校黑板报上看到你的作文”,貌似成绩好,其实是严重偏科,成绩很一般。
我中学毕业时还没有考大学一说,全凭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外婆家成分高,我怕劳动,表现好不了,自知推荐无望,便托人在邻乡供销社找了一份工作。那是物资匮乏的年代,猪肉、糯米、食糖、香烟、白酒等全凭计划供应,我的岗位正好可以走后门,教过我的老师,都把我当成能人,节假日常结伴骑自行车到邻乡找我,有的写手令让子女来找我,我总是想尽办法满足他们的要求。如此,我便成了老师们眼中的好学生,每次回母校像进了娘家庄,到处有人请我吃饭。
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那时我已在社会上混迹了三年,学到的文化一大半还给了老师,故与继续深造擦肩而过。幸亏我的中学老师都非等闲之辈,我多少也学到了一点皮毛,以致后来凭鼓捣破文章的功夫走进县市主管部门,接着凭学到的分析问题处理问题能力,赢得领导好感,被授了一顶小帽,也就这么滥竽充数地混了几十年。因此,我对母校、对老师,始终是有感情的。
南阳中学弃址异地重建了,据说高楼大厦挺时尚。我是没兴趣去观赏的。母校是学子的根校友的魂,老校友们魂萦梦牵的,永远是那个浸润着半个多世纪人文情怀的南阳中学,那里有我们师长和同学的身影,那里有我们的芳华和理想。唉,母校不在了,让我们在梦中寻找她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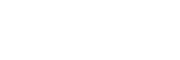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