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片来源:网络
西团南团瓜蒌团,朱家团陈家团戚家团,头灶七灶八灶,张家墩子李家舍,老家的这许多诸如此类的地名,都带有咸味,它们都在海水里泡过。它们最初的居民,有我落难至此的先辈。夜枕潮声眠,昼煎卤水生,故乡曾在波涛间,先辈原是煮海人。
1000年前,身为泰州西溪盐官的范仲淹,在泰州知州张纶的支持下,对筑于唐代的捍海堰进行加固、重修。这条两百多公里的海堤,对于阻挡海水西侵,功不可没,后世为了铭记范氏修堤之功,将这条捍海堰改称范公堤。我弄不明白的是,一代代的父老乡亲,都对范仲淹崇敬有加,可在范氏修堤之后,历经几百年的变迁聚集,他们居住的那些团、灶、墩、舍,才逐步形成,而且,依然不时遭遇海潮的光顾。范公堤拦截海潮护良田,可惜君家却在海堤外。不错,海堤也有阻挡上游洪水的功能,但用张纶的话说,“涛(海水)之患十之九,潦(洪水)之患十之一”,范公堤对堤内的居民良田,护卫之功甚大,而于当时在堤外煮海为业的零星居民,对于后来迁徙此地加入煮海行列的我的先辈们,则意义不大。
600年前,朱元璋建立了大明王朝,受曾经和他争夺天下的张士诚的牵连,我的先辈们在内的一大批“吴王”的子民被从苏州发配到范公堤以东这片不毛之地。其时,范公堤已失去阻挡海水的功能,因为海水逐年东迁,潮水能够达到的地方,已经距离范公堤30多华里。从范公堤向东北,有一条流经故乡全境的河流,弯弯曲曲,绵延百数十里而入海。这河流原来是海滩上的一条潮水涨落的自然通道,河名斗龙港,其关于神牛和恶龙搏斗的故事,隐约地揭示出先辈们在这片土地上遭受海水肆虐的艰难的生存状态。曾听爷爷和我说过,他的爷爷本来弟兄三个,那日,他十八岁的大哥和十六岁的二哥烧盐之余,去海滩上挖蛤蜊,涨潮了,赶忙回头,却不知在走过多少次的地方,二哥意外地陷进一片沼泽,大哥走过去拉二哥,结果,弟兄俩身陷沼泽,被潮水吞没。为此,他的妈妈哭瞎了双眼。
范公堤以东最早新建的海堤,距今只有100余年的历史,为清末民初南通著名实业家张謇来大丰废灶兴垦时所筑。在这之前,一遇大潮,海水倒灌便在所难免,以至于上世纪中叶,团灶墩舍周围的河水,还又咸又涩。
故乡的居民并不都是因为洪武遣散来自苏州。盐民张士诚是在元末揭竿而起的,而史籍上关于张起事前,是泰州草堰场张家墩子人的记载,说明我的故乡在那时已经有了相当数量的居民。没有海堤的遮掩,却能在海滩上安家,这安家之处必定是海滩上的高地,自然的或者人工垒出的,或者在自然的基础上再垒土加高的,总之,那时诸如张家墩子的团、墩、灶、舍等人群集聚地已经存在。当时的原住民看到从城里而来的外地人时,不知是否有如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们看到城市居民下放农村时的那种好奇和兴奋。我们目睹了那些在城里生活惯了的城市平民在村子里的艰难和窘迫,也目睹了他们后来和知青一样,在返回城里之前的激动和兴奋。早已认同自己“乡下人”身份的我们这些“土著”,虽然对农村生活有深刻的切肤之痛,但彼时,却对那些离乡背井而来的城里人充满更深的怜悯和同情。
张生煮海是一个美丽的故事。我的先辈们煮海,却是一群被强制为业的盐民,在海边荒滩,从苦涩的海水中,煎熬出源源不断的白花花的财富,而自己却赤贫如洗地过着的一种蛮荒原始、毫无生命保障的生活。我不知道先辈们在原籍何以为生,但从当时相对富庶发达的州府之地,被驱赶到这里,不说物质上的艰苦卓绝,就是那种精神上的郁闷和失落,都足以让人沉沦而至万劫不复。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作为童子军和妈妈她们一起在村子西面、学林伯伯家门前一块地里平一个“无主”之坟。此坟就是一个大一点的土疙瘩,多年无人打理。学林伯伯于心不忍,在每年清明节前,给它添些土,挖个坟头。当我们一群妇女和儿童将其挖开,在地面向下一尺多深,竟然有了惊人的发现:一个用青砖砌成的墓椁!因为怕触犯这神秘的地下建筑,妇女儿童们撤退,并喊来了在另一块地里做活的学林伯伯和干爷爷几个,我们收工回家。我至今都为没有能够亲眼看到砖郭里面有什么而遗憾,但后来听学林伯伯和干爷爷他们说,他们挖出一大堆砖头后,理出了一堆尸骨,在尸骨骷髅头旁边,有一块方形的大砖,上面用刀刻着两个不太清楚的字。他们不认识,把这个神秘的砖头拿给做阴阳先生的三余爷爷看过。我工作之后,曾为这事儿找到当年已经年近一百的三余爷爷,问当时砖头上写的什么。三余爷爷告诉我,那两个字是“南歸”,那个墓里埋的是我们刚刚从苏州迁来不久的祖宗,因为祈求魂归故里,就在用来做枕头的方砖上刻了这两个字。我问他那块方砖的去向,他说看过后被干爷爷带走了——他说,这块方砖和那个墓里挖出的青砖,后来被干爷爷砌到了厨房的墙上。
先辈们没有得到重新返城的机会,他们像树一样在这块泛着碱花的土地上扎下根来,竟至长出茂密的丛林。他们煮海水为财富,变荒滩为良田,他们来的时候或许只是一对对年轻的夫妇,挑着最简单行李,但是,一代代的繁衍,他们的血脉已绵延成高低错落,大小不一的村庄。这些村庄,最初只是同宗同族的聚居,后来,逐步成为以族姓为主的多姓氏混合居住。这些被叫做团、墩、灶、舍的村庄,名称的前面冠有他们的姓氏,他们和村庄一起,一度成为在这块土地上崛起的一道独特风景。
当时在这块土地上,团、墩、灶、舍之间,还有许多同步诞生的寺庙。比较出名的有七灶的龙王庙,陈家团和瓜蒌团之间的祖师庙,西团的晾网寺,戚家团的云齐庵。我对于龙王庙和祖师庙的院落和屋宇,被供奉其间的泥塑金身的菩萨,在庙宇里修道的僧人,至今留有依稀的印象。龙王庙和祖师庙后来都被改建成了学校。祖师庙是一所中心小学,我曾在这里度过从七岁到十三岁的六年小学时光。2014年,市政协组织撰写《魅力大丰》,我亦受命参与其事。我为了写祖师庙,曾邀请小学学长顾正宏、王加和两先生同到母校故址寻旧,但秋风瑟瑟,那个承载着我们童年记忆的地方,除了两棵被大丰市人民政府列为文物保护的历经沧桑白果树,便是一片高低不一的庄家地。——先辈们筚路蓝缕,却有佛光普照。当年,这些佛教领地的存在,如果说是一种信仰的见证,那么,是否可以说,正是它们,支撑起先辈们倾颓的人生。
现在故乡的土地上,公路纵横交错,横平竖直的民居,井然有序,几无二致地排列着。风光了几个朝代的范公堤,剩下被作为标本保留的极短的一段,其余都融入204国道的路基。高速公路、高等级公路越境而过,现代化的海堤,随着港口建设的发展,如同一条绿色的巨龙,于海潮奔涌处凌空而起。只是团、墩、灶、舍,所有的村庄,寺院庙宇,都已被历史的大潮荡涤得不留痕迹。所幸记忆还在,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乡村建制的恢复,使许多老地名在消失数载后又重新得以回归;对于渐行渐远的故乡,这是能够辨别地面方位的、闪烁在高远天空的温馨星光。
吟七律一首,结束本文:
团场灶墩是故乡,依稀梦影旧时光。
吴王势去子民徙,洪武时来蝼蚁殃。
煮海常生千里念,捕鱼难解三春荒。
白驹过隙沧桑巨,且喜眼前风送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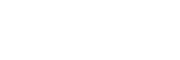














网友评论